张爱玲说:“我的母语,是被北边话和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。”她的上海话是后学的,虽然她一向被视为上海都市文学的代表,但从接触张爱玲的小说起,总觉得她的行文用字里,时不时就蹦出一种安徽味。张子静说:“然而母亲和姑姑走了。我和姐姐由保姆带着。”她母亲和姑姑1924年离开家去欧洲留学,张爱玲不过四岁,正值学习语言的关键期,就这么被安徽的保姆、女佣包围着,那种影响,也许不像她学上海话那么刻意,但大抵是“润物细无声”——不知不觉沁到皮里。去美国之后,张爱玲总提安徽方言。
这种方言,实在是她过去生活的一部分。《怨女》里,银娣一家说一口家乡的侉话。《小团圆》里,有那句大名鼎鼎的合肥土白:“不做摪搞啊?”“摪”也是凭音对上的字,意思是怎样,听惯了上海话和普通话的人,再听这个话,难免会侉气。
张爱玲与弟弟吃饭,女佣则敦促:“快吃,霞子没得吃呵!”“霞子”,在合肥话里指孩子。叫女儿有时候叫“大姐”,“我家大姐”,女儿小的时候也有叫“小大姐”的。张爱玲用在小说里,算是土白,还是侉气,但那种质朴的与生活气息,却从一两个字的变动和语气的变换中油然而生。还有合肥土白里“啊”字的发音方式,也被张爱玲分析过,“合肥话拖长的‘啊’字,卷入口腔上部,搀入咽喉深处粗粝的吼声,从半开的齿缝里迸出来”,古怪的戏剧化。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,也生活在安徽方言里,有时候她也会用合肥土白打趣女仆一下:“嗳,韩大妈!好啊?我好欧。”发“欧”字音,嘴唇形成圆形,一种客气在里面。
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在写作过程中,张爱玲时不时就用到皖北的俚语,比如“有红似白”,指脸色白里透红;皖北人爱把猪嘴叫“猪拱嘴”,有时候形容人嘴唇厚,或者嘴型过于突出,就打个比方,说“切切倒有一大盘子”。梦见放鞭炮张爱玲搬过来,放在《金锁记》里,后来改成《怨女》还在用。《小团圆》里还提到家里女佣说“跑反”,大概是指1937年之后,日军全面侵华,安徽是“重灾区”。老辈的安徽人都知道“跑反”,也叫“跑日本鬼子反”,常常是夜里动身逃难。直到1990年,张爱玲七十岁,在《联合报》上发《“嗄?”?》,又提到安徽方言,“苏北安徽至今还保留了‘下饭’这形容词,说某菜‘下饭’或‘不下饭’,指有些菜太淡,佐餐吃不了多少饭”。小时候她听到合肥女佣说“下晚”,总觉得奇怪,下午四五点钟称“下晚”,她以为是下半夜,其实类似于“向晚”,靠近晚上的意思,古文有: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
张爱玲晚年吃得很简单,在美国,中式馆子不多,自己做一是太麻烦,二是未必能做出那个味道。于是,早年吃的美食——家里做的安徽小吃,一不小心就全都从记忆里跑出来了。《小团圆》里的韩妈会做一般厨子不会做的菜,合肥空心炸肉圆子,火腿萝卜丝酥饼,“过年总是她蒸枣糕,碎核桃馅,枣泥拌糯米面印出云头蝙蝠花样,托在小片粽叶上”,色香味俱全。还有冬天的麦芽糖,“韩妈绞了一团在那双筷子上,她仰着头张着嘴等着,那棕色的胶质映着日光像只金蛇一扭一扭,仿佛也下来得很慢”。《雷峰塔》里提到蒸鸡蛋,“舀碗水蒸个鸡蛋骗骗霞子们”。皖中人对于蒸鸡蛋有种特别的爱好,尤其爱蒸给小孩子吃。
1980年,张爱玲特地谈过吃。说有一次她姑姑想吃“黏黏转”,是从前田上来的人带来的青色的麦粒。田上的人从安徽来,家里的田有的在无为(安徽地名),张爱玲深以为“无为”这个地名很有哲学意味(庄子就是安徽人?无为名取“思天下安于无事,无为而治”之意)。她小时候也吃田上来的“大麦面子”,暗的面粉,用滚水加糖调成稠糊,有一种焦香,她认为远胜桂格麦片。
张爱玲是“知恩图报”的。向暖,张爱玲的一生了太多冷漠。安徽的方言与美食,其实在潜意识层面折射了张爱玲对于幼年时期点滴小温暖的怀念。父亲、母亲、姑姑,她曾爱过,也曾受伤,变成一身怨念,无可逃遁。数来数去,张爱玲的童年生活中,也只有那些看似不相干的老妈子给了她一些不痛苦的、可接受的、相对轻松的暖意。方言和美食,仿佛时光机,一下就把张爱玲拉到当初那些小场景中,让她想起那些女仆,照顾她,为她好,忠心。张爱玲喜欢朴素的规则,“文官提笔安天下,武将上马定”,君君臣臣父父子子,女仆也就像个女仆。从小带过张爱玲的何干(《小团圆》里韩妈的原型?),曾经是张的祖母李菊耦身边的丫鬟,一这么带过来,是个老仆,对张爱玲很有感情。她带张爱玲一床睡,早上起来就帮着张爱玲舐眼睛,像母牛对小牛一样。尽管张爱玲并不喜欢这样,但这曲曲折折的关心与情谊,怎么会体会不到?
“韩妈”在张爱玲家多少有点面儿。儿子女儿外孙女上城里找事,都是住在“九莉”家,她儿子一度还通过主家的关系,找到了工作,只不过没多久就丢了。张爱玲和“韩妈”还有一些近乎黄段子的小幽默。“有一天韩妈说:‘厨子说这两天买不到鸭子。’九莉便道:‘没有鸭子就吃。’一声断喝:‘吓咦!’‘我不过说没有鸭子就吃。’‘还要说!’”日常生活中语言上的滑稽,到老了都不能忘。
更何况何干是该出手时就出手:张爱玲因为要求留学被父亲在阁楼,患了痢疾,若不是何干去找张父劝说,后果不堪设想(她去向张的继母讨药,给了一盒万金油);张爱玲逃出父亲家,去找母亲,因为怕爱玲的继母清理东西,一个星期后,何干把张爱玲小时候的一只首饰箱送了过来。后来何干离开了张家,走时张爱玲去送,约在静安寺电车站见,张爱玲顺便先到车站对街著名的老大昌,把剩下的一块多钱买了两色核桃糖,两只油腻的小纸袋,作为送给何干的临别礼物。给完张爱玲就后悔,还不如直接给钱,虽然不多,但给一点是一点。何干找张爱玲要了一只她学校定制的装零食的小铅皮箱,张连忙答应了。她们都没有哭,但都知道,这就是永别了。从前张爱玲“有许多发财的梦想,要救九林韩妈出去”,可坎坷命运,谁又救得了谁?一直到晚年,张爱玲想起来,都还觉得自己亏负她。女佣在隔壁洗衣间的水泥地上,洗被单、帐子时的声音她一直记得,被单撞上搓衣板,“咯噔咯噔咯噔”……她没能让她过好日子。
在张爱玲的晚年著作中,何干的代言人“韩妈”大量存在着,张爱玲对她的偏爱,可见一斑。其实不难理解,何干是对她好过的人,再一个,何干曾经是老太太身边的人,从安徽来,目睹了当年老太太和老太爷的种种,是一部活的历史。张爱玲对何干的喜爱,深层次说,是源于她对家族历史的喜爱和认同。晚年她出《对照记》,这个时候她的生命已经倒计时了,她说:“我没赶上看见他们,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,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,看似无用、无效,却是我最需要的。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,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。”点点滴滴,安徽的方言、安徽的美食、安徽的女佣,一鳞半爪也好,管中窥豹也罢,它们像是一条条支流,一丝丝,给张爱玲提供了寻根的线索。
暴风雨瞬间就能一切,而她通过寻找与想象找到的那个藏在历史深处的贵族之家,钟鸣鼎食、琴瑟和鸣、其乐融融,却永远不会变,永远站在她身后,尽管仿佛海市蜃楼,但还是给予她受伤的灵魂一座温暖的堡垒。
文章由325棋牌提供发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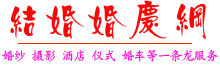



 删除。
删除。
网友评论 ()条 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