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建业的情人周冰徐家胡辣汤,合我的口味,在凤城四西口,铺面小,早上才有,我每周都去一次。这天再去,房子不见了,一排房子,都不见了。被拆迁了。我走这么远过来,饭没吃成,站住站了一会儿,就离开了。
我遇见的还少吗?这太正常了。在城市里,一些地方的格局,也是覆盖了原有的样式才逐渐形成的。岁月往前走,已经老旧,似乎定型了的群落,又面临改变。留下残砖烂瓦,留下废弃的沙发,掉了底的靴子,撕了一半的明星的画张,被清理,被清空。似乎按下去了删除键。几乎一夜间,就由新的建筑和街道取代,甚至把人口都替换了。来处和去处,都发生了逆转,一个家族,在述说过往时,就有了多种可能,有了叹息和欣慰。
意外也有,不值得奇怪。还是能看到,本来要消失的,却在拖延中,在滞后中,得以喘息,而出现逆转。规划在图纸上的一揽子的面貌,并非例行公事,甚至带有强制,在限定的时间内,却未能完全实现。常常有遗留,有放弃,最终的结果,就像漏网之鱼,就像视觉盲区,在一些貌似整齐划一的公园,楼盘,开发区的边角,一部分原来的房子,巷道,样本一样,提取物一样,竟然还在,竟然保持了下来。这些局部的人,这些被忘却了的区域,和随后出现的大的区划,格格不入,又能共处一个空间,原有的生活方式,延续着,并且还不怎么明显地、试探性地,介入到了身旁的新世界。更有意思的是,由于一个项目结束之后,再也没有专门的组织者,把这些残留的存在当做任务,来干预,来动员,使得这样的两个不同,怪异地组装在一起。我如果偶然来到这里,能看出先后吗,能解读出变迁的绝对和并不绝对的坚守吗?
曾经是主体,曾经在一方土地上,有自身的高度、坡度,哗哗的水流和吆喝,却像附着物,尴尬地衬托着新建成的楼盘。留下留不下,还是留下了。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起来前,是建材市场,集中了许多灯具、板材和石材批发商。如今的园子很大,每个方向都能进来。可是,就在西南头,就在一组胖硕的帝王塑像旁,挨着围墙,竟然有一座墓。不是古墓,也不是新坟。水泥板的墓碑,有几十个年头了吧。我第一次经过看见,有些吃惊。第二次就不奇怪了。什么原因不知道,反正,能搬迁的都搬迁走了,这座墓还在。墓主人有后人吗,清明,十月一,会有人来祭奠吗?
大明宫的北边,是东西向的玄武。这条宽阔,只是到了东头,收窄,一大半应该是面的上,是两个单位的院墙和房子,不知什么原因,还留守在原地。车子到了这里,都会减速,对于过马的,倒还方便,几步就跑过去了。不过,这条平时车流量少,很少发生拥堵。这算什么,我在莲湖公园里,还看到了一户人家呢,就开在公园里,门口一棵树,丝瓜蔓牵引下来,树阴大,丝瓜长,过日子的景象看着喜人。过去,逛公园得买票,省下多少不说了,来这里的人,看风景,人家坐在口,既看了风景,也看了人。
一定时间段里,变迁的发生是必然的。或者由于放弃,要么来自战乱。更多的,似乎是在变新变好的过程中,一种似乎温和的腾挪。那又如何。别说民居,就是皇家,多么浩大的格局,多么繁复的营造,不也埋进土里,化为灰烬了吗。我可以触碰的例子,不就是我常来的大明宫遗址吗。即使是遗址,不也要通过拆迁,才能呈现出那么一点残骸么。私人的屋宇,想要长久存在,难度大,公家的呢。社会更替,也有一次次的和。我前不久才知道,就在大明宫遗址的南头对面,过太华,有一个类似198的艺术中心,也是了废弃厂房形成的。我去了,发现这个大厂区,原来是纺织厂,历史久远,名字就叫大华·1935。数字正是建厂的年头,够悠久了。在里头,我看到了小资味的小剧场,看到了咖啡馆,还看到了新华书店的仓库。都是利用原来的车间、工房布置的,原来的砖瓦,墙体也基本上保留。我还看到了织布机,蒸汽机,看到了纺锤和纱锭。都集中在一个也是旧工房的展览馆里,里头没有几个人看。这么大一个厂,说没有,也就没有了。那么多的工人,哪里去了。那么多的织机,哪里去了。来这里,我不是怀念,我和这里,没有发生痛感的关系,虽然我少年时穿过的背心,睡过的床单,可能来自这里。也不是凭吊,虽然这也是一处遗址。工业的更新和,总会有淘汰发生,这难以。我只是走走看看,像一个闲人。如果这个工厂的废墟不被赋予另一种利用价值,也许我什么也看不到。可是,我看到了,就是难受一阵子,又有什么意义呢。
只有具体的人,有体温和情感的身体,感受才会深切。城市,对许多人,伤到了根。可是,拿到钥匙的回迁户,是多么兴奋啊。还有的地块,虽然清空了,却不见动静,十年八年过去的都有。那些临时安置的住户,该有多么焦虑啊。在,叫撂荒,在城里,是土地闲置。土地被人忘记了,杂草披头散发出来,没给吃药一样,药吃多了一样。地闲着,也是金贵的,不能全交给杂草,得有人着。按说开发的阵势发大水一般,有一块地,赶紧盖楼呀,可是,在上走,随处可见圈起来没有动静的土地。凤城三我常走,靠南边的边,挡板架得高,看不到里面。有一处地段,是公交车站,墙内向外发散强烈的尿骚味。我估计,年头久了,住在板房里的人,临时方便,一天天的,便固定下来,一个人的肥料,早晚累积,又不处理,只是肥沃了荒地,也捎带一下过人。这里原来有一排铺面,是饭馆,修车铺,电器铺,彩票售卖点,早晚都热闹。有一家叫五指羊的烧烤,有一年的夏天闹地震闹得厉害时,不敢回房子,我坐了半晚上,喝了一肚子啤酒。旧的没有了,新的不出现,成了现在的样子,也被我看习惯了。还有些被征用了的地段,围墙开了豁口,走捷径的人钻出钻进,没有人。一片闲地,不担心丢失什么,走就走了。在里头的老头,闲不住,挑选出土质凑合的,开垦出一块两块,种菜是吃呢,种花是看呢。四周围拢的,是杂草,还是杂草。
钉子户这个词,这些年提到的多。城市,不愿搬走的,坚强留守,成为孤绝的标志。开元上的一片地方,原来也是一个村子,开发拆迁,一村子人,都安置到别处去了,只有一户不走,修到这户人家前面,中断了,前后的都了,就是不能打通。靠北边的段,很长一段时间,变成了驾校的场。到了晚上,则有成群的大妈跳广场舞。旁边的便道,人能走,车子经过就勉强。拆迁如潮,凡是不愿意,而选择对抗的,都有原因,要么补偿谈不拢,要么就觉得在自己这边,就应该留下:这是我老先人传下来的,就不走,咋的!这户人家的原因,倒是奇怪,是和上的亲戚打官司输了,不服气,就僵持住,要求法院重新判,不然就不走。真的就没有走,真的就没有被强制拆除。七八年了,我每次经过这里,都要好奇地看看这栋二层的建筑,从侧面看过去,能看到门前的棚子,有时有孩子在玩耍,有时看见洗过的衣服晾晒在高处。听说由于断水断电,这户人家照明点蜡烛,吃水都是提着塑料桶到附近一个公厕里接水。我挺同情这户人家的,甚至,还对他们的意志力有些敬佩。可是,因为影响了周边天然气管道的铺设,旁边小区的一些人家联合起来向上反映,还在这户人外悬挂,也没有结果。这户人家周边,杂草茂盛,夏天跟疯了一样长,就像围了一圈草木的屏障。
得再说一说杂草。和野草一样,杂草也是自己长出来的。不叫野草,却叫杂草。野草和杂草,其实是同义词。不过,区别还是有的。杂草可以叫野草,而野草却不一定是杂草。野草还有一片天地,有日月星辰的期待,杂草却由不得自己,不是想长就能长。杂草没有身份,就跟寄居在城市边缘的人一样。也许一直没有机会,就一直隐身在城中村的角落,长眠着,蛰伏着。杂草不如野草,没有野草的,立足之地不确定,也无从争取,人们无意间的和疏忽,才使杂草得到生机。那些的人,那些失却家园的人,不也是这样吗?掌控命运,却一次次跌倒,一来,在哪里安放一张床成了未知。可是,人是活的,该应变了,就能想到办法,杂草更善于把握着因为而出现的意外。
于是,只要出现空地,杂草就能长满。也见到铺了水泥的面,一个小坑,一道裂缝,也有杂草萌芽。而人们培育的青草,无论牧草,还是草坪用的草,得浇水,修剪,喷药,动不动就长死了。轻一些的,会发生退化,干枯变黄。杂草为什么不害病?杂草的生命力,如此,真是给一点阳光就能咬烂钢铁,没有雨水,在石灰里也能榨出甘露。归结一句:没被驯化。即使为杂草,也还是自己,只服从自然的律令,谁的都不听,的也不听。杂草就这样立足于世界,流浪在任何能去的地方。不过,我们吃的麦子和水稻,也是老祖先从杂草里选育的。我们春种秋收,吃着杂草的种子。不经过人工,打不下这么多粮食,不经过劳动,我们会太闲。人闲生。那样,人就该退化,老化了。也有可能,人得到解放,又没事干。就发明,就艺术,那样的话世界更美好,还是掉呢?这个话题就大了,还是说杂草吧。
工地上堆起土堆,就长草。不光春季。有时在冬日,向阳背风的一面,也冒出点点绿。土堆也许十天半月就清理了,杂草照样不计后果,照样长。要是保留一年半载,杂草大草帽一样。杂草长一人高的,多是淹没狗身子,兔子身子的。杂草生长,土堆的分量减轻了,还是加重了,还是没有变化呢。城里的杂草,是多余的。也许在冬天,点一把火,呼啦卷过去,留下的是黑色的根茬。几年前的一个春节,孩子工作在外,我和妻子无聊,干啥都没心思,有一天胡乱走走到朝北的贞观,两边的工地已经休工,四下里不见一个人影,我抱了一盘鞭炮,就在一个倒卧着枯草的大土堆上点着,炮响了很久,响过了,我的心里,还是空落落的。现在,这一带不再冷清,楼房早就盖起来了,人都住上了。现在,我很少再走这条。
天地转,光阴迫,人换了,就什么都换了。本来很熟悉的,是那么陌生,即使身在其间,也觉得和自己关系不大,或者说,只是符号和符号的关系。人也是符号,也是符号的一种。这个,变化太快,我脑子反应慢,四肢的动作也慢,就像诗人唐欣的诗句:我追不上,追不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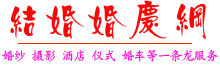



 删除。
删除。
网友评论 ()条 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