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91年3月5号,厌倦巴黎生活的高更从马赛出发,独自一人来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(又名塔希提),在这里让高更重新找回了绘画的和冲动。
希瓦欧阿岛是马克萨斯群岛的花园,岛的中心是那个叫阿图奥纳的小镇,高更的欢愉小屋在阿图奥纳的中心,有一个很大的花园,希瓦欧阿的市长,为了推动岛上经济的发展,重建了欢愉小屋和高更博物馆,高更的一生,便在那些画和故事里得到复活。
1901年,那个叫保罗·高更的男人,一见到希瓦欧阿就想到了梵高:天啊文森特,就是这个地方,我们在阿尔勒梦寐以求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啊!111年后,当我们降落在希瓦欧阿这个小岛时,它依旧那么孤僻地待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,热情的人像它的花一样,丰腴多汁,充满诺阿的甜香。
这块土地,面对着湾,背靠着两座雄伟的山峰,流经一侧的是马克·马克波利尼西亚土语里小溪流的意思,对面的阿纳克荒岛,就像一头入睡的抹香鲸,高更和梵高工作室的梦想就要实现啦。经过6个星期的努力,这座欢愉小屋终于大功告成,有两层,一楼是厨房和雕塑室,二楼是画室、卧室和卫生间,锥形的屋顶,是用草编成的,大门顶上的长木板上就写着“欢愉之屋”,和一些优美的野兽和杂草、女人。当然,还有两条高更语录,“有了爱情你就会幸福”“保持神秘你就会快乐”。欢愉小屋的建成,简直更是让捶胸顿足,他号召岛上的居民一律远离这么一个附体的人,而高更却乐不可支,从此算是结下了高更和之间的对峙。欢愉小屋,如今是一座高更博物馆,里面没有高更原画,但有着高更的一生,和几乎所有高更作品的临摹画。
墓园里常年开着芬芳的鸡蛋花,有洁白的花瓣、淡淡的黄心。可当地人都把鸡蛋花叫做高更花,他们说,高更很喜欢这淡淡香味久久不散的花儿,在高更墓四周,都是一树一树沉甸甸的鸡蛋花,落满了他的墓前。总有人轻轻地来,默默地抹去尘埃,捡起新鲜的鸡蛋花放在他的墓碑上,没有繁复的思念,没有肃穆的哀悼,甚至偶尔的,会有几个年轻的土著女孩子在墓前,静静地坐下来,轻轻地唱着莫名的歌曲,这样的归宿,才是高更想要的吧。墓地边上,立着一尊雕像,是高更自己的作品死亡,手持幼小的狐,脚下踩着一匹狼,像是一尊花瓶儿。从高更墓望出去,抹香鲸一般的阿纳克荒岛依旧在沉睡,湾里依旧蔚蓝入梦,到处都是鸡蛋花的香味,高更最后的大溪地,就在这里了。
这个小岛甚至没有几家咖啡馆、餐厅等可以去的地方,我们只能坐在一家杂货铺前吃着沙沙作响的雪糕在这里,法国的身影远得模模糊糊的,就是大根大根的法国长棍面包都有煎饼朴素的味道。可是,杂货铺里,却传出了纯正的法语声,一曲让人微醺的曲调,明明是欢愉,却感觉是在痛哭。
高更的画中,最美丽的自然就是那些大溪地的女人,高更说,她们大大方方地看着你,充满,毫不胆怯,她们好客……是的,大溪地女人,太平洋的风和赤道的阳光了她们古铜色的皮肤,润泽的花环,,加上美丽的微笑。我们看着她们,示意要,于是她们就停下来,美丽地笑了起来,这些如同阳光般灿烂大溪地女孩啊,从来就没有因为时光而改变过。
帕皮提的机场,就像南太平洋诸岛国一样,大花布裙的歌者和舞者正迎候在入关处,眼睛也会跳舞的女孩儿轻快地扭动着身躯,空气中浮动着的栀子花香,炙热的太平洋风情迎面扑来,花香就从一个竹编的大盘子里传出来,搁满了又香又白的花,它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国花。
来客不论男女老少,皆学了当地人,把花往耳后一插有的插在左边,有的插在右边,相互看看,也不知道到底谁对了。一同下飞机的帕皮提女孩儿海娜忍不住笑了,教我们,如果是女生,戴在左边表示已婚,告诉其他男士不要追求自己;戴在右边是未婚,但暂时不想被追求;戴在中间是给自己心仪的人看的,表示她需要他。可对于游客,戴在哪边又何妨?在那朵娇俏的白花衬掩下,再疲惫沉重的面孔模样,瞬间便蒙上了一层轻盈,花香了昏昏的睡意。
海娜,将右耳那一支有点儿萎靡的红花拿下,取了一朵白色的栀子花重新插在左边,那你到底是未婚还是已婚呢?海娜调皮地说,在外面,她是未婚,现在她男朋友要来接机了,她就是已婚。海娜,有着大溪地女孩儿一头蓬松的卷发,极具挑逗的眼神儿,一刻没有安静,“我男朋友是个在银行工作的法国人,他常常说你为什么不能像法国女人一样优雅呢?”“可如果你喜欢法国女人的优雅,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,直接去找法国女人好了。”说得极是,如果高更喜欢巴黎的调调,他为什么要来大溪地呢?
最热闹的去处,是帕皮提市场。早上的时光异常繁忙,占地7000平方米的帕皮提市场是个两层楼的建筑,却常常都被四射的活力和生活的气息占据得满满当当。挂在货摊上的草帽、编织袋子,一堆堆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水果和花朵,都有着和主人衣饰一样的鲜艳又热情的色彩。那些水灵灵的芋头、蔬菜、植物和鲜鱼虾贝,色泽饱满,充满了雀跃的生机。上到顶层,那里波利尼西亚风格的手工制品和艺术品,都在等着被人认领回家。
可市场里的精彩,并不是这些商品。还记得高更画里的女人们吗?在帕皮提的中央市场,那些宛如从高更画作里走出来,正忙着编织花环的女人们,无论身材胖瘦都裹了五颜六色的花裙,和着市场里色彩饱满的一切,都那么不吝于遮盖一丝丝生命的颜色;还有那个男人,穿上湖蓝晚礼服式的长裙,留了长长的发,跷着兰花指,神色淡然,婉转地在菜摊前吟唱着什么,在喧闹的市场里,高高低低的歌声,居然清晰可闻,周围一圈女人,都地看着他。
从小被男扮女装的男子,曾经,也是高更迷恋上大溪地的理由之一,他那幅《希瓦欧阿岛巫师》里的巫师郝普阿尼,就是这样的形象女性化的长发插着小花,身上的大红斗篷在背后燃烧;而让高更有点儿骄傲,也有点儿哭笑不得的是,法国海军少尉热诺,高更在帕皮提的早期朋友之一,却告诉高更,毛利人根据他的长发和头上戴的莫希干人的小帽子。王闻
与梵高、塞尚合称为印象派三杰的高更,生于巴黎,逝于马克萨斯群岛的希瓦欧阿,梦见包被偷在经历了63天的海上旅行之后,他到达大溪地,并且留了下来,大溪地的浓郁风情和美貌女子,成为了高更画中,最具有特色的一笔。
在大溪地拍完《叛舰喋血记》之后,马龙·白兰度就在当地买了一处居所,并娶了一个大溪地女郎,开始了大溪地美好的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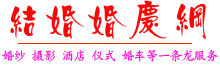



 删除。
删除。
网友评论 ()条 查看